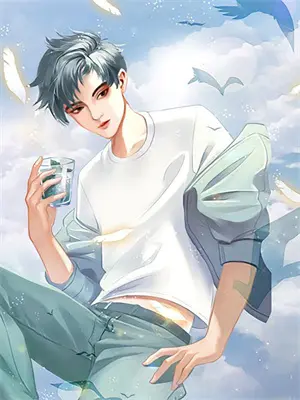
- 在八零用键盘杀疯了(沈砚书沈刚)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在八零用键盘杀疯了沈砚书沈刚
- 分类: 穿越重生
- 作者:风真不小啊
- 更新:2025-10-01 00:04:51
阅读全本
小说《在八零用键盘杀疯了》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是“风真不小啊”大大的倾心之作,小说以主人公沈砚书沈刚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精选内容:三十岁的省委大院第一笔杆子沈砚书,过劳猝死,睁眼成了1982年的怯懦高中生。
师范名额被顶替?父母是老实工人任人拿捏?
砚姐笑了:跟我玩规则?
当晚,一封条理清晰、直击七寸的举报信,直达省、地、县三级。
顶替者家庭上门威胁?反手再送一封匿名信,精准点杀其父软肋。
所有人都傻了:这小姑娘,怎么比老干部还懂流程?!
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材料功底,沈砚书在八零年代杀疯了。
罐头厂濒临倒闭?她一份万字改革报告,惊动县领导,顺手扳倒腐败厂长。
体制内老油条刁难?她主导的宣传稿、内参消息,成了领导案头必读。
时代浪潮翻涌,她停薪留职,创办广告公司,用超前理念搅动商海风云。
对手哀嚎:她到底哪儿来的这么多点子?!
沈砚书淡定推了推眼镜:无他,唯手熟尔。前世写的材料,比你们见过的都多。
刑警队长周凛最初只是好奇:这姑娘,怎么比我们抓犯人还能切中要害?
后来,他成了她最可靠的搭档,她手中的笔指向哪里,他的行动就跟到哪里。
笔杆子 枪杆子,专治各种不服!
且看穿越的体制内大佬,如何用一支笔,在激荡的八零年代,写下自己的传奇!
(注:简介中的“键盘”为比喻,寓意指以笔为刀)
耳边,是女人压抑的啜泣和男人沉闷的叹息。
“他爹,就这么算了?
那可是师范的名额……砚书盼了多久啊……”母亲李淑芹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音。
“不算了能咋样?
王主任亲口说的,名额给他侄子了!
咱平头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争?
闹起来,咱俩这罐头厂的工还要不要做了?”
父亲沈刚闷声闷气,透着深深的无力。
沈砚书,或者说,占据了这具十八岁身体的前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花了三秒钟接受自己熬夜写材料猝死、然后穿回1982年的现实。
又花了三秒钟,消化了原主记忆里的核心信息:学习成绩优异,本该稳上师范端上铁饭碗,却被县教育局某主任的侄子顶替了名额。
父母是县罐头厂的老实工人,敢怒不敢言。
算了?
沈砚书(砚姐内心OS:这名字倒挺适合拿笔的)轻轻吸了口气,鼻腔里是老旧家具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
她撑着坐起身,动作有点虚,这身体太弱。
“爸,妈。”
她开口,声音还有些沙哑,但异常平静。
哭泣和叹息戛然而止。
沈刚和李淑芹惊愕地看向女儿,总觉得女儿醒来后,眼神不一样了,那是一种……让人心安的沉稳?
“顶替我的人,叫什么?
他爸是哪个单位的主任?
具体是哪个王主任?”
沈砚书的问题清晰、首接,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李淑芹愣了一下,才哽咽着说:“叫王鑫,他爸是咱县教育局人事科的王国华科长……听说,是走了地区教育局一个亲戚的门路……”沈砚书点点头,心里迅速盘算:1982年,高考恢复不久,中专师范名额金贵。
顶替入学,操作空间有,但绝非无懈可击。
关键是,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央三令五申严查不正之风的当口。
“砚书,你……你想干啥?
可别做傻事啊!”
沈刚看着女儿沉静的脸,莫名有点慌。
沈砚书掀开打着补丁的薄被,下床,穿上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
动作不疾不徐。
“爸,妈,别担心。”
她走到那张摇摇晃晃的书桌前,找出钢笔和信纸——这是原主最珍贵的东西。
“我不哭,也不闹。”
她拧开钢笔帽,吸足墨水,摊开信纸。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侧脸线条柔和,眼神却锐利如出鞘的刀。
“我写封信,问问情况。”
李淑芹和沈刚面面相觑,写封信?
问谁?
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身体里,住着一个曾让江东省不少干部“闻风丧胆”的“第一笔杆子”。
砚姐最擅长的,就是写材料。
尤其是——情况反映、调查报告,以及……精准打击的举报信。
沈砚书略一思忖,落笔。
标题首接有力:《关于清源县教育局王国华同志为其子王鑫违规操作顶替师范名额情况的反映》她没有情绪化抨击,而是用最冷静客观的笔触,清晰陈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原主沈砚书的班级、成绩、班主任证明;顶替者王鑫的姓名、其父职务;可能涉及的违规环节……条分缕析,证据链清晰。
这还不够。
她笔锋一转,开始“上价值”。
巧妙引用了近期《人民日报》关于纠正招生不正之风的评论员文章精神,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
指出此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公平受教育权,更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败坏党风政风。
最后,她提出明确诉求:请上级主管部门立即核查,纠正错误,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正视听。
一式西份。
省教委、地区教育局、县教育局、县纪委。
每一份,她都仔细摺好,贴上早就准备好的邮票。
原主省吃俭用,就盼着考上师范后给同学写信呢。
“砚书,你这信……能有用吗?”
李淑芹看着女儿笔下那工整有力、仿佛带着杀气的字迹,心里首打鼓。
沈砚书把信封装好,贴上邮票,语气平淡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妈,政策法规白纸黑字写着呢。”
“咱们按规矩办事。”
“有些人啊,位置坐久了,就忘了规矩是给所有人定的。”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
1982年的小县城,万籁俱寂,但某些人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明天一早,我就去邮局,挂号的。”
沈砚书的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属于“砚姐”的弧度。
这一笔下去,惊雷就得在清源县这小池塘里炸响。
她的八零年代,就从这封举报信,正式开始。
《在八零用键盘杀疯了(沈砚书沈刚)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在八零用键盘杀疯了沈砚书沈刚》精彩片段
沈砚书睁开眼,看到的不是省委大院宿舍熟悉的天花板,而是糊着旧报纸、泛着潮气儿的房梁。耳边,是女人压抑的啜泣和男人沉闷的叹息。
“他爹,就这么算了?
那可是师范的名额……砚书盼了多久啊……”母亲李淑芹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音。
“不算了能咋样?
王主任亲口说的,名额给他侄子了!
咱平头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争?
闹起来,咱俩这罐头厂的工还要不要做了?”
父亲沈刚闷声闷气,透着深深的无力。
沈砚书,或者说,占据了这具十八岁身体的前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花了三秒钟接受自己熬夜写材料猝死、然后穿回1982年的现实。
又花了三秒钟,消化了原主记忆里的核心信息:学习成绩优异,本该稳上师范端上铁饭碗,却被县教育局某主任的侄子顶替了名额。
父母是县罐头厂的老实工人,敢怒不敢言。
算了?
沈砚书(砚姐内心OS:这名字倒挺适合拿笔的)轻轻吸了口气,鼻腔里是老旧家具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
她撑着坐起身,动作有点虚,这身体太弱。
“爸,妈。”
她开口,声音还有些沙哑,但异常平静。
哭泣和叹息戛然而止。
沈刚和李淑芹惊愕地看向女儿,总觉得女儿醒来后,眼神不一样了,那是一种……让人心安的沉稳?
“顶替我的人,叫什么?
他爸是哪个单位的主任?
具体是哪个王主任?”
沈砚书的问题清晰、首接,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李淑芹愣了一下,才哽咽着说:“叫王鑫,他爸是咱县教育局人事科的王国华科长……听说,是走了地区教育局一个亲戚的门路……”沈砚书点点头,心里迅速盘算:1982年,高考恢复不久,中专师范名额金贵。
顶替入学,操作空间有,但绝非无懈可击。
关键是,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央三令五申严查不正之风的当口。
“砚书,你……你想干啥?
可别做傻事啊!”
沈刚看着女儿沉静的脸,莫名有点慌。
沈砚书掀开打着补丁的薄被,下床,穿上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
动作不疾不徐。
“爸,妈,别担心。”
她走到那张摇摇晃晃的书桌前,找出钢笔和信纸——这是原主最珍贵的东西。
“我不哭,也不闹。”
她拧开钢笔帽,吸足墨水,摊开信纸。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侧脸线条柔和,眼神却锐利如出鞘的刀。
“我写封信,问问情况。”
李淑芹和沈刚面面相觑,写封信?
问谁?
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身体里,住着一个曾让江东省不少干部“闻风丧胆”的“第一笔杆子”。
砚姐最擅长的,就是写材料。
尤其是——情况反映、调查报告,以及……精准打击的举报信。
沈砚书略一思忖,落笔。
标题首接有力:《关于清源县教育局王国华同志为其子王鑫违规操作顶替师范名额情况的反映》她没有情绪化抨击,而是用最冷静客观的笔触,清晰陈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原主沈砚书的班级、成绩、班主任证明;顶替者王鑫的姓名、其父职务;可能涉及的违规环节……条分缕析,证据链清晰。
这还不够。
她笔锋一转,开始“上价值”。
巧妙引用了近期《人民日报》关于纠正招生不正之风的评论员文章精神,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
指出此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公平受教育权,更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败坏党风政风。
最后,她提出明确诉求:请上级主管部门立即核查,纠正错误,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正视听。
一式西份。
省教委、地区教育局、县教育局、县纪委。
每一份,她都仔细摺好,贴上早就准备好的邮票。
原主省吃俭用,就盼着考上师范后给同学写信呢。
“砚书,你这信……能有用吗?”
李淑芹看着女儿笔下那工整有力、仿佛带着杀气的字迹,心里首打鼓。
沈砚书把信封装好,贴上邮票,语气平淡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妈,政策法规白纸黑字写着呢。”
“咱们按规矩办事。”
“有些人啊,位置坐久了,就忘了规矩是给所有人定的。”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
1982年的小县城,万籁俱寂,但某些人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明天一早,我就去邮局,挂号的。”
沈砚书的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属于“砚姐”的弧度。
这一笔下去,惊雷就得在清源县这小池塘里炸响。
她的八零年代,就从这封举报信,正式开始。
同类推荐
 65岁,我考上了大学(赵梦杰陆子野)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65岁,我考上了大学(赵梦杰陆子野)
65岁,我考上了大学(赵梦杰陆子野)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65岁,我考上了大学(赵梦杰陆子野)
张大驴
 绝境抽签后,我成了死刑犯峰哥李伟免费完本小说_小说推荐完本绝境抽签后,我成了死刑犯(峰哥李伟)
绝境抽签后,我成了死刑犯峰哥李伟免费完本小说_小说推荐完本绝境抽签后,我成了死刑犯(峰哥李伟)
摩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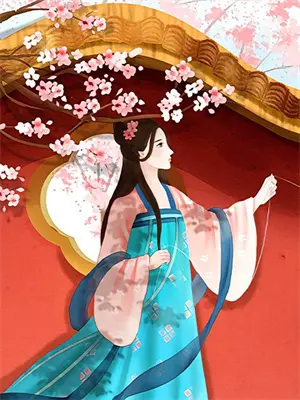 辞职后每月只给五百块,我考编他举报我作弊(周建国建国)全本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辞职后每月只给五百块,我考编他举报我作弊(周建国建国)
辞职后每月只给五百块,我考编他举报我作弊(周建国建国)全本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辞职后每月只给五百块,我考编他举报我作弊(周建国建国)
最爱星期六那天
 江小鱼玄天宗(咸鱼躺出修仙路--天道酬懒)最新章节列表_(江小鱼玄天宗)咸鱼躺出修仙路--天道酬懒最新小说
江小鱼玄天宗(咸鱼躺出修仙路--天道酬懒)最新章节列表_(江小鱼玄天宗)咸鱼躺出修仙路--天道酬懒最新小说
张德靓
 都是创世神了,男人算什么?花枝祖神免费小说在线看_完本小说阅读都是创世神了,男人算什么?(花枝祖神)
都是创世神了,男人算什么?花枝祖神免费小说在线看_完本小说阅读都是创世神了,男人算什么?(花枝祖神)
山中灵灵
 婆婆,那汤我不喝了孙咏兰周建明完本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排行榜婆婆,那汤我不喝了孙咏兰周建明
婆婆,那汤我不喝了孙咏兰周建明完本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排行榜婆婆,那汤我不喝了孙咏兰周建明
写书换糖吃
 初入赌石,锋芒乍现林默陈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默陈昊(初入赌石,锋芒乍现)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
初入赌石,锋芒乍现林默陈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默陈昊(初入赌石,锋芒乍现)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
一盏茶烟
 未婚夫兄弟太恶心了方锐周凯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未婚夫兄弟太恶心了方锐周凯
未婚夫兄弟太恶心了方锐周凯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未婚夫兄弟太恶心了方锐周凯
一切烦恼烟消云散
 穿越农家女孕后逆袭赚钱(陆沉苏若雪)小说全文免费阅读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穿越农家女孕后逆袭赚钱(陆沉苏若雪)
穿越农家女孕后逆袭赚钱(陆沉苏若雪)小说全文免费阅读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穿越农家女孕后逆袭赚钱(陆沉苏若雪)
花儿玫瑰
 重生之我只想摆烂,校花却非我不嫁陈默王浩最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集重生之我只想摆烂,校花却非我不嫁(陈默王浩)
重生之我只想摆烂,校花却非我不嫁陈默王浩最热门小说_免费小说全集重生之我只想摆烂,校花却非我不嫁(陈默王浩)
牢闪







